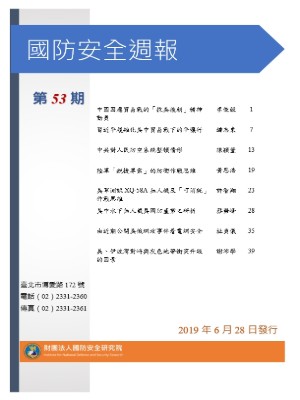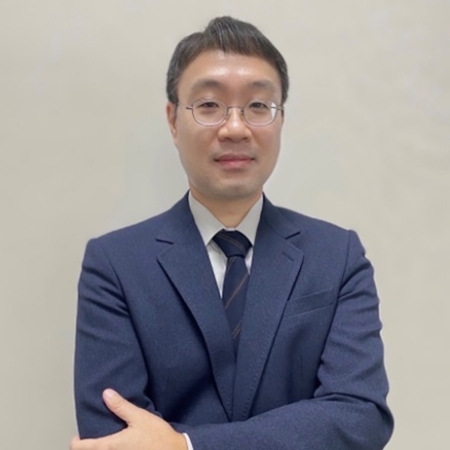中國因應貿易戰的「抗美援朝」精神動員
2019.07.01
瀏覽數
79
壹、新聞重點
美國宣布於2019年5月10日起將中國2,000億美元的輸美產品之關稅由10%調高至25%後,中共中央宣傳部電影衛星頻道(CCTV-6)隨即自5月16日起,連續5日以反美的韓戰戰爭片《英雄兒女》、《上甘嶺》、《奇襲》、《鐵道衛士》以及韓戰紀錄片《冰雪長津湖》取代原訂播放之影片。6月20-2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至北韓進行國事訪問,並於21日赴位於平壤的「中朝友誼塔」參謁。該塔為北韓於1959年興建,目的是紀念1950年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與韓戰。習近平訪問北韓,特別是參訪「中朝友誼塔」之舉,不無呼應此一「抗美援朝」聲浪的意味。值得注意的是,6月18日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與習近平通話,確定兩人將於6月28-29日在日本大阪舉行之G20高峰會期間會晤後,CCTV-6於19日臨時改播以中美軍人合作抗日為主題的愛情電影《黃河絕戀》。此舉在網路上引發討論與嘲諷,有論者指CCTV-6已成為「中美關係晴雨表」,但這也體現中國以媒體影響民意對美國觀點的操作手法。 [1]
貳、安全意涵
一、中國對貿易戰的回應反映其大國形象受損
所有的外交政策都涉及集體認同的闡述與詮釋,亦即回應「我們」是誰、和「他們」有何不同、「我們」要往哪裡走、「我們」和特定「他們」的關係等問題,因此需要一套關於國家或/和民族的敘事或論述。若此一關於自我的故事被否定而無法穩定延續,則自我可能產生「生存的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引發恥辱、挫折、或失敗的感覺。將這些不利且不幸的結果歸咎於某個負面意象的「他者」,從而確保或重申自我的正面認同,是國家實踐的一種常見方式。中國(與台灣)在國族歷史的建構上不僅宣揚文明的光榮,也紀念中國的衰弱(如百年國恥、不平等條約、東亞病夫等概念),並將近代中國的歷史描述為由恥辱到光榮的過程,即是一種藉由「國家的不安全」(national insecurity)證成國族復興的必要性之策略。 [2]
隨著美中貿易戰的持續進行與升高,中國被迫不斷回應,也需要一套敘事合理化當前局勢。以2019年6月2日中國國務院發表之《關於中美經貿磋商的中方立場》白皮書為例,其論據主要是指責美國「挑起對華經貿摩擦損害兩國和全球利益」以及「在中美經貿磋商中出爾反爾、不講誠信」;相形之下,中國則是「始終堅持平等、互利、誠信的磋商立場」。[3] 透過諸如「霸凌vs.善良」、「不理性vs.理性」、「反覆vs.誠信」等二元對立,白皮書建構了截然不同的美中形象(如下表)。這顯示美國自貿易戰開打以來對中國的指責如盜竊智慧財產權與強迫技術轉讓等,否定或傷害了中國一向以來自詡之「負責任大國」的自我認知,因此在對貿易戰的回應上,不僅訴諸經貿利益對兩國乃至全球的重要性,更在認同層次上著力。沿此邏輯,中國越是強調兩國在身分認同上的差異,就越是反映其對於自身形象受損的焦慮。
表、《關於中美經貿磋商的中方立場》白皮書建構之美中形象
資料來源:李俊毅整理自《關於中美經貿磋商的中方立場》白皮書。
|
|
美國的形象與主張 |
中國的形象與主張 |
|
兩國的本質 |
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將自身利益訴求強加於他國;貿易霸凌行徑殃及全球 |
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本著善意和誠信 |
|
對中美經貿關係的看法 |
挑起中美經貿摩擦;認為中國採取不公平、不對等的貿易政策 |
從維護中美經貿關係的大局出發,保持理性、克制的態度;貿易逆差當作「吃虧」是算錯了賬 |
|
對另一方的作為 |
得寸進尺,採取霸凌主義態度和極限施壓手段;以所謂國家安全的「莫須有」名義,連續對華為等多家中國企業實施「長臂管轄」制裁;潑髒水、拆台、極限施壓 |
為捍衛國家尊嚴和人民利益,不得不作出必要反應;不得不採取加徵關稅的措施 |
|
對談判的態度 |
違背共識、出爾反爾、不講誠信;不負責任;隨意指責中方「倒退」 |
展示了極大誠意;始終以誠信為本;雙方要互諒互讓,共同尋找解決分歧的辦法;談,大門敞開;打,奉陪到底 |
內文/圖片、表格名稱
由於貿易戰涉及對中國自我認知的否定,中國乃有從事精神動員的必要。[4] 中國前財政部長、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因批評「中國製造2025」而於2019年4月4日突遭免職,是中國因貿易戰而緊縮言論的例證之一。進一步來說,前揭白皮書主張「對於貿易戰,中國不願打,不怕打,必要時不得不打,這個態度一直沒變」,此一立場延續中國對國際衝突與戰爭的基調,也使之能和「抗美援朝」的歷史記憶相呼應。中國《環球網》早在2018年4月7日,即以社論「用打抗美援朝的意志打對美貿易戰」主張兩國已從事「戰前動員」,而以中國今日的實力,能讓美國「重新認識中國體制團結全國人民痛擊外部經濟強權挑戰的特殊能力」。
CCTV-6在2016年的市場佔有率最高達9.5%,並有81.4%的受眾為年齡在25-44歲的青壯人口,既是中國家庭娛樂的重要平台,也是其國產電影的主要消費管道之一。中宣部因此透過CCTV-6以電影呼應時事,繼而從事愛國教育與精神動員;CCTV-6亦不諱言,「我們在用電影這樣一種文藝作品呼應當下的時代」。CCTV-6在2019年5月間播放紅色電影時,透過官方新媒體平台1905電影網稱,「中國精神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實現中國夢,不僅要求我們具備強大的物質基礎,也要求我們具備強大的精神力量」;該報導亦認為透過前揭電影,「我們不僅緬懷了革命先烈的先進事蹟,更堅定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不畏強權,維護民族獨立和民族尊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決心」。在美中競爭的氛圍下,這些言論連結「抗美援朝」與貿易戰,使貿易戰儼然成為實體的戰爭;影片中的戰爭意象以及對英雄的歌頌,則試圖將中國民眾代入霸權抗爭的脈絡,從而合理化中國當前因貿易戰而有之社會與經濟壓力,並要求中國民眾持續的忍耐、付出與支持。 [5]
參、趨勢研判
一、中國建構的美中形象使之難以在貿易談判中妥協
美國政府發動貿易戰之目的不僅在於平衡雙邊貿易,也意在以經濟與科技反制中國崛起。這些要求固非中國可全盤接受,惟中國以二元對立的方式建構美中關係,也限縮了自身可回應的方式。從《關於中美經貿磋商的中方立場》白皮書的論述來看,中國政府試圖營造一個負責任、理性、尊重、與不卑不亢的大國形象。此舉旨在使中國享有道德上的制高點,從而將貿易戰的源起以及歷次經貿磋商的失敗歸咎於美國。然而,此一策略也限制了中國的行動自由,因為正確的一方並無向錯誤的一方屈服之理。中國政府若應美國(與國際社會)的要求而做出變革,便可能被中共內部的勢力與國內不滿的民意指為屈從於霸凌者,從而提高政治風險。因此中國面對美國政府的施壓,除了訴求美國「同中國相向而行……共同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之外,似乎也只能透過消耗戰的方式,或是如《環球網》前揭社論所述,「這場貿易戰是中美一起打,一樣痛」,讓美國體認到兩敗俱傷的後果而終止其攻勢。即使中國與美國達成某種(暫時)協議,此協議也必須能被解讀為中國的勝利,否則難能說服國內社會。
二、中國操作歷史記憶的難度日益增加
歷史記憶的操作本意是透過愛國與精神教育動員社會,對內維繫政府的正當性,對外增加談判的籌碼,但此類操作有其風險。「抗美援朝」的論述策略一旦操作成功,固然可增加中國政府的正當性,但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成為主要的社會氛圍後,不僅任何被中國視為對之不利的美國(乃至國際社會)舉措,都將被賦予「反中」的意涵,與此基調不符的人、事、物,也可能成為被攻擊的對象。1999年5月8日,中國駐前南斯拉夫大使館遭美軍轟炸;2005年4月間,日本政府核准右派撰寫之歷史教科書與「國有化」釣魚台燈塔之舉;2012年8月日本政府宣稱收購釣魚台而將之「國有化」,這些都曾引起中國民眾激烈反彈,是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被激化後,難以受政府控制之例證。2019年5月間,部分與美國有關的電影或節目發生異動,如《復仇者聯盟4:終局之戰》上映一個月即不再延長、美劇《權力的遊戲》第8季第6集因故延播、電視劇《帶著爸爸去留學》在上映前臨時撤檔等,都可視為是貿易戰下的政治正確考量所致。
中國政府當前可能意識到過度操作的危險,因此並未不斷宣揚「抗美援朝」的論述。前述在「川習會」可望成局的情況下,CCTV-6改播電影《黃河絕戀》之舉,不無和緩兩國關係之意。惟一國自我的敘事必須穩定,中國若持續隨美中局勢變遷而再三改變其對美國的看法,將導致民眾在訊息接收上的混淆甚至錯亂。當前中國的網路與社群媒體不乏嘲諷CCTV-6肆意引導輿論的操作手法,長此以往將增加中國精神動員的難度。習近平近年來多次批評各地地名充滿「崇洋媚外」風氣,使中國多個地方政府於2019年6月間進行「清理整治不規範地名」的行動,要求整頓使用外國地名、人名或西文翻譯命名的地名,以彰顯國家主權和文化屬性。此舉引發輿論反彈,使中國民政部於6月21日出面澄清,可見操作民族主義與意識形態的風險。
[1]〈習近平將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新華網》,2019年6月1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6/17/c_1124635405.htm;〈習近平和彭麗媛參謁中朝友誼塔〉,《新華網》,2019年6月2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6/21/c_1124655341.htm;朱加樟,〈【中美貿易戰】央視連播抗美援朝電影:呼應當下展現對美不退讓〉,《香港01》,2019年5月19日,https://tinyurl.com/y42jxz68;彭琤琳,〈【貿易戰現轉機】央視突改播《黃河絕戀》:二戰中美軍人愛情故事〉,《香港01》,2019年6月19日,https://tinyurl.com/y5pa8ftt。川習會則訂於6月29日舉行。
[2] Cf.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Alanna Krolikowski, “State Personhood in Ontolog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A Sceptical View,”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2, No. 1 (July 2008), pp. 109-133; William Callahan, “National Insecurities: Humiliation, Salvatio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Vol. 29 (2004), pp. 199-218.
[3]〈關於中美經貿磋商的中方立場〉,《新華網》,2019年6月2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6/02/c_1124573295.htm。
[4]根據我國《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14條,精神動員指「結合學校教育並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培養愛國意志,增進國防知識,堅定參與防衛國家安全之意識」。爰此,中國以「抗美援朝」的電影宣揚愛國主義和民族意識,是其精神動員的一環。
[5]〈社評:用打抗美援朝的意志打對美貿易戰〉,《環球網》,2018年4月7日,http://opinion.huanqiu.com/editorial/2018-04/11795194.html?agt=15422;祥燎,〈中國最任性的電視台,永遠猜不到它要播什麼〉,《微信上的中國》,2019年5月20日,https://chinaqna.com/a/81830;王兆陽,〈【電影抗美】四天四部抗美援朝電影:CCTV6擬明播《鐵道衛士》〉,《香港01》,2019年5月18日,https://tinyurl.com/y54oo6h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