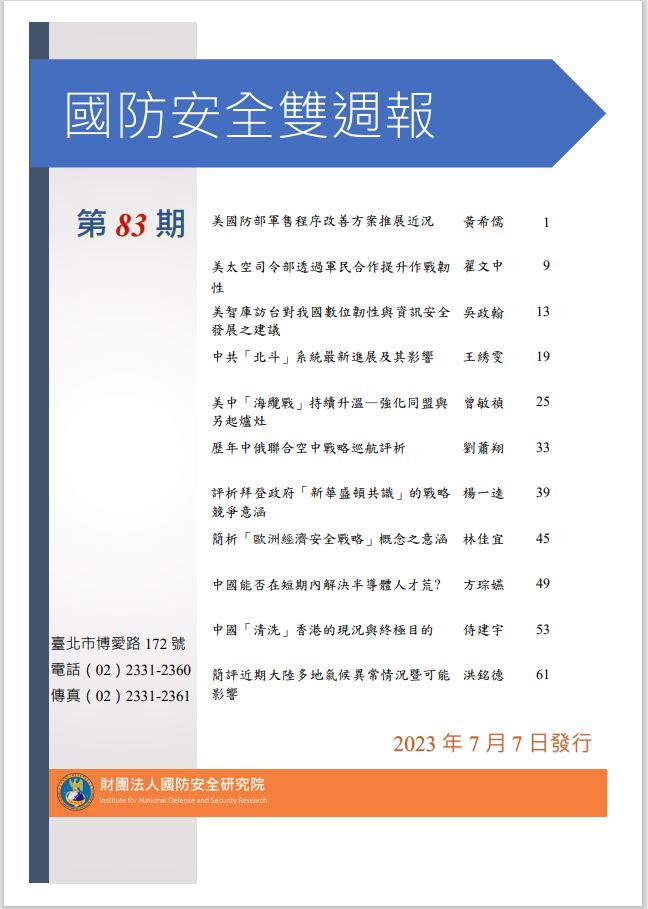評析拜登政府「新華盛頓共識」的戰略競爭意涵
2023.07.07
瀏覽數
4559
壹、新聞重點
美國經濟學者威廉遜(John Williamson)於1989年提出「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旨在針對當時的拉美與東歐國家進行經濟改革,手段包括貨幣緊縮政策,減少政府介入市場與管制,降低公共預算,推動市場、金融與貿易自由化,開放外資,促進外資自由流動,與國有企業私人化等。[1]即便「華盛頓共識」之後被證明,過度追求自由化市場驅動的發展模式其實不利國際經貿秩序穩定,亦有害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長。但不可諱言,「華盛頓共識」在當時不僅被「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 WB)接受,其中的自由市場競爭驅動,私有制,與小政府等「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思維,依舊係過去數十年來,全球化分工的核心價值。[2]
若回顧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於2000年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演講,可發現美國過去相信,以美國為首的「華盛頓共識」與國際制度,將可引導中國行為,而透過全球化打開中國市場,更符合美國利益。[3]然上述關於「華盛頓共識」與全球化分工的理念,在美中高度競爭的今天似乎已至盡頭。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於2023年4月27日,以「重振美國經濟領導地位」(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為題,揭示拜登政府「新華盛頓共識」(New Washington Consensus)的政策方針,其核心內涵旨在勾勒出未來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競爭策略。[4]本文試圖探析「新華盛頓共識」指涉的全球化風險,與未來美國與中國的競爭策略。
貳、安全意涵
一、全球化分工弱化美國經濟安全與競爭優勢
蘇利文在論述「新華盛頓共識」的過程中點出,過去以「華盛頓共識」為核心的全球化分工,不僅衝擊美國經濟安全,更形成四大挑戰。[5]第一,美國的工業基礎與戰略物資供應鏈,因過度追求自由市場競爭的模式而被掏空。高度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同時,美國的就業機會與生產能力亦逐步外移,形成對外「依賴」(Dependence)的缺陷。
第二,以WTO為首的全球化經貿制度並沒有改變「非市場經濟」(Non-Market Economy)的中國。中共依舊凌駕於資本之上,並從國際自由市場中大量獲利,延伸經濟影響力。中國更以政策銀行挹注資金與產業補貼方式,破壞自由市場的競爭秩序,導致美國不僅失去製造業的生產能力,在關鍵技術競爭上,如乾淨能源、關鍵基礎建設,與生物科技等,已失去優勢。
第三,中國正利用全球化分工,與各界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強化其政治影響力。蘇利文指出,全球經濟上的整合與「互賴」(Interdependence)並未讓解放軍停止擴張,亦或限制威權國家的侵略行為。反之,中國似乎正逐步降低自身對外部世界的「依賴」,同時強化外部世界對中國的「依賴」。
第四,「華盛頓共識」引導的全球自由貿易,並沒有落實讓勞工階層受惠的「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反加深貧富差距,催化「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雖然貧富差距與「民主倒退」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依然充滿辯論,但研究已顯示兩者間有一定的關聯性。
綜合觀察,蘇利文雖然表面上係檢討「華盛頓共識」對美國與國際經貿秩序的影響,然其實質內涵卻係針對中國如何在美國引領的全球化分工下獲利與擴張,而美國又如何在國際分工,與委外製造中失去競爭優勢。
二、美國政府需強化產業投資與擴大支出
蘇利文認為,為解決上述因中國等「非市場經濟」行為者破壞的國際經濟秩序,與重振美國競爭優勢,美方需執行增加政府投資與支出的「產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換言之,「新華盛頓共識」就是相信政府引導優於自由市場競爭的大政府手段。美國將針對特定產業,包括乾淨能源、關鍵礦物、半導體與晶片,與國防產業等供應鏈,挹注資金,厚實美國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美國不單投資自身產業,也將擴大投資新興經濟體、盟友與理念相近之夥伴,試圖建立不「依賴」中國的供應鏈韌性。蘇利文在演講中甚至直接引用,強調政府應適時干預經濟活動的「凱因斯」(Keynesian)概念:「擠入效應」(Crowding In Effect),論證擴張的政府支出可大幅增加民間投資。
事實上,早於蘇利文提出「新華盛頓共識」前,「拜登經濟學」(Bidenomics)當中擴大政府投資以抗衡中國的舉措已十分明顯。拜登政府於2021年通過的《兩黨基礎建設法案》(The 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Deal),係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聯邦公共建設投資,其中包括投資交通建設(660億美元)、電動車充電樁(75億美元)、電動校車與巴士(5億美元)、港口與機場修繕(170億美元)與乾淨能源與電網(650億美元)等項目。[6]拜登政府於2022年8月通過的《晶片法案》(CHIPS Act),總投資金額高達2,800億美金,其中包括520億美元的半導體產業補貼,號稱美國史上最大半導體投資。[7]同年通過的《降低通膨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將耗資4,300億美元投資,全面扶植美國的乾淨能源與醫療產業。[8]白宮經濟顧問狄斯(Brian Deese)認為,上述美國強化政府投資與支出的核心目的在於,重建美國的產業生產能力。[9]
三、美國追求經濟自主的「經濟民族主義」再起
以「新華盛頓共識」作為論述基礎的「拜登經濟學」,象徵美國「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再起。傳統上,文獻傾向將「經濟民族主義」置於自由開放貿易政策的對立面,因其與保護本國製造商的「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密不可分。然研究發現,「經濟民族主義」並不反對自由開放的貿易政策,因其核心主張係透過政策,讓國家可以免於外國的經濟干預,形成經濟上的獨立、自主與自由,甚至可以「自給自足」(Self-Sufficiency)。[10]以當前全球供應鏈受制於COVID-19疫情、俄烏戰爭、與威權國家「武器化」(Weaponize)產業與經貿「互賴」關係的情勢來說,追求經濟與供應鏈上的自主與自由,其實係某一種面向的經濟韌性。換言之,當外在危機發生時,一國的產業與供應鏈可以吸收衝擊,並自由地不受制於該危機,仍可持續運作與生產的狀態,就是「經濟民族主義」追求的經濟自主。整體來說,追求「經濟民族主義」的目的在於杜絕產業與供應鏈對外「依賴」,讓外國沒有機會進行經濟干預或脅迫。
達到「經濟民族主義」追求經濟自主的方式,需透過政府適度的介入市場經濟活動,扶植「自給自足」的生產力,因生產力即國力。當美國發現無論如何批判中國或與其競爭,最終都擺脫不了中國在醫療用品、戰略物資、電池、資通訊科技產品,與關鍵基礎建設等供應鏈牽制時,「經濟民族主義」政策自然浮出檯面。習近平於2020年10月31日更表示,中國需要建立供應鏈的殺手鐧技術,拉緊國際產業鏈對中國的依存關係,形成可對外斷供的反制與嚇阻能力。[11]面對中國領導人公開「武器化」供應鏈的宣言,不僅美國,各界都將思考推動經濟自主與獨立的可能性。
參、趨勢研判
全球大政府時代的來臨
相信政府適度干預市場經濟活動,建立自主經濟韌性,優於過度追求自由市場競爭的大政府思維,正在全球擴散。在COVID-19疫情期間,全球政府支出高達17兆美金,合計占全球GDP的16%。[12]隨著俄國入侵烏克蘭,「武器化」糧食與能源供應鏈,與中國一系列「經濟脅迫」(Economic Coercion)行為,都讓各國開始透過政府支出、投資與補貼政策,強化自身產業的獨立性與自主性,降低對俄國、中國等威權勢力供應鏈的「依賴」。
以歐盟來說,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Ursula von der Leyen)於3月20日提出的「去風險」(De-Risking)內涵,旨在重振歐洲在醫療、數位、乾淨能源等供應鏈上的自主與獨立能力,降低對中國技術與市場的依賴。[13]范德賴恩的說法亦符合歐洲議會智庫對於「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所給予的定義——歐盟自主行動的能力,在重要戰略的政策領域中,不倚賴其他行為者的自主行動,包括國防、經濟與民主價值的擁護。[14]
作為自7月1日開始的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西班牙總理桑切斯(Pedro Sánchez)於6月19日宣稱,發展歐盟的「再工業化」(Reindustrialization)將係其首要任務。[15]桑切斯認為,歐盟需要分散其貿易與投資合作關係,擺脫在能源、衛生、數位技術和食品等關鍵領域對外的過度「依賴」。桑切斯的「再工業化」,其實就是大政府思維「產業政策」的運用。未來美歐將如何在政府適度調控下建立可靠、自主與獨立的供應鏈生態系統,需持續觀察。
[1]John Williamson, “The Strange History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Vol. 27, No. 2, 2004. pp. 195-206.
[2]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3]“Full Text of Clinton’s Speech on China Trade Bill,”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9, 2000, https://shorturl.at/nqyE9.
[4]“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The White House, April 27, 2023, https://shorturl.at/ajmuU.
[5]Ibid.
[6]“FACT SHEET: The 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Deal Boosts Clean Energy Jobs, Strengthens Resilience, and Advances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8, 2021, https://shorturl.at/ezTX9.
[7]Makena Kelly, “Biden Signs $280 billion CHIPS and Science Act,” The Verge, August 9, 2022, https://shorturl.at/tNQ09.
[8]Chelsey Cox, “Biden Signs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nto Law, Setting 15% Minimum Corporate Tax Rate,” CNBC, August 16, 2022, https://shorturl.at/fkS48.
[9]“Remarks on a Modern American Industrial Strategy by NEC Director Brian Deese,” The White House, April 20, 2022, https://shorturl.at/mEHST.
[10]左正東,〈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問題與經濟民族主義的再檢視〉,《國際關係學報》,第32期,2011年7月,頁51-90。
[11]〈習近平: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新華社》,2020年10月31日,https://rb.gy/ajdyg。
[12]“The World is Entering a New Era of Big Government,” The Economist, November 18, 2021, https://rb.gy/v9eve.
[13]“Speech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on EU-China Relations to the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and the European Policy Centre,” European Commission, March 30, 2023, https://rb.gy/g8al2.
[14]Mario Damen, “EU Strategic Autonomy 2013-2023: From Concept to Capacity,” European Parliament, August 7, 2022, https://rb.gy/tr9ct.
[15]“Pedro Sanchéz Presents the Priorities of the Presidency of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La Moncloa, June 19, 2023, https://reurl.cc/Ovry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