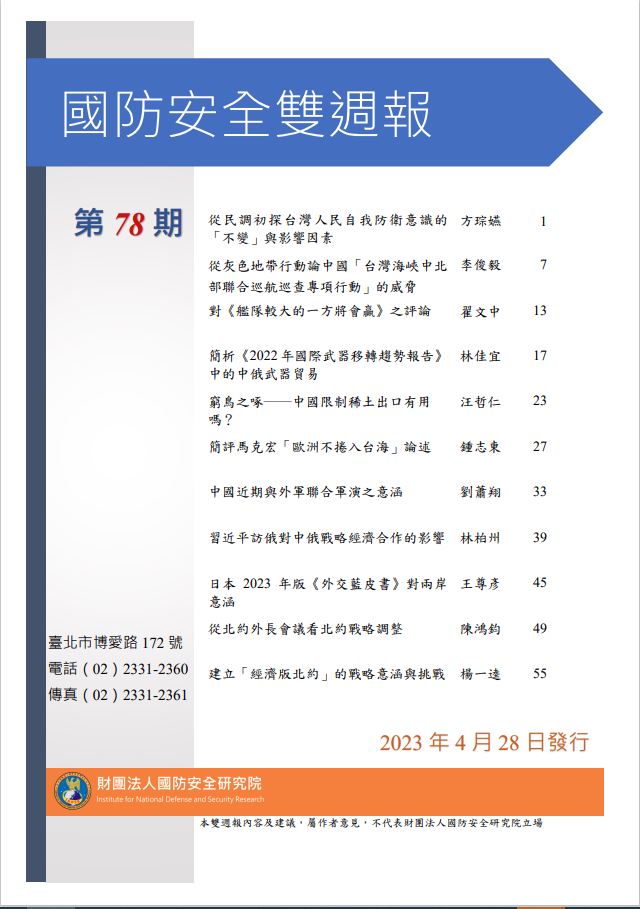建立「經濟版北約」的戰略意涵與挑戰
2023.05.03
瀏覽數
3138
壹、新聞重點
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學者古德曼(Matthew Goodman)與雷諾茲(Matthew Reynolds)近期發表研究呼籲,針對中國日益擴張的「經濟脅迫」(Economic Coercion)舉措,美國應率先號召國際理念相同的夥伴,建立「拒絕脅迫」(Coercion-Denial)的反制「聯盟」(Alliance)機制。[1] 前英國首相特拉斯(Liz Truss)亦公開提出類似概念,提倡國際應以「七大工業國集團」(G7)為基礎,建立抗衡中國脅迫性經濟的「經濟版北約」(Economic NATO)。[2] 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以下簡稱「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與前美國駐北約大使達爾德(Ivo Daalder)更撰文指出,參與美國主辦「民主峰會」(Summit for Democracy)的成員應仿效「北約」公約第五條,制定經濟版「北約」的第五條公約,在符合國際法與「世界貿易組織」(WTO)規範條件下,集體防禦中國的經濟報復手段。[3] 在此脈絡之下,本文試圖探析各界呼籲建立「經濟版北約」的戰略意涵與未來挑戰。
貳、安全意涵
一、威權國家的「經濟脅迫」衝擊「自由國際秩序」
從歐洲到美國,各界開始呼籲建立「經濟版北約」的緣由係因威權國家的「經濟脅迫」,已對強調多邊合作、制度與規範的「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產生衝擊。「經濟脅迫」係指一國透過施行或威脅施行限制與阻礙貿易及投資的行為,試圖迫使另一方改變,或產生特定的政策選擇。[4] 在全球化分工,供應鏈互相依賴的今天,「經濟脅迫」已成為威權國家挑戰「自由國際秩序」的慣用手段。俄國在俄烏戰爭中「武器化」(Weaponize)糧食、穀物與能源供應鏈,惡意限制出口貿易,造成國際市場的價格動盪,即為威權國家「經濟脅迫」的鮮明案例。中國2010年因民運人士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而貿易制裁自挪威進口的鮭魚,與2012年中菲於黃岩島海域的爭端事件,誘發中國以檢疫問題為由,緊縮對菲律賓香蕉的進口等事件,更係中國「以經逼政」的經典案例。
「自由國際秩序」的國際法原則亦受到該等「以經逼政」的挑戰。依據《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宣言》(Declaration on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cerning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各國有義務避免使用軍事、政治、經濟或其他形式脅迫其他國家行為者的政治獨立性。[5] 1974年聯合國通過的《國家經濟權利及責任憲章》(Charter of Economic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當中亦明定,任何國家不得使用經濟、政治或任何其他類型的舉措脅迫另一個國家。[6] 換言之,當中國透過貿易報復手段,企圖迫使其他主權國家(例如立陶宛)依循符合中國利益的對台交往政策,已構成上述挑戰國際法原則之情事。
二、建立類似「北約」的集體「經濟安全」聯盟時機或已成熟
威權國家近年來向外擴張的經濟脅迫手段不僅凸顯「世界貿易組織」(WTO)中「爭端解決機制」(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效力不彰的問題,更反映出該等威脅已跨越「地理鄰接性」(Geographical Proximity)的侷限,全球沒有局外者。換言之,即便西歐國家在軍事安全上,感受到來自中國或俄國的威嚇,不如印太區域行為者或東歐國家來的強烈,但中俄經濟脅迫的威脅仍可直接衝擊西歐大國。因此,國際社會需要一個新的集體「經濟安全」(Economic Security)同盟,應對與嚇阻橫跨「印太」(Indo-Pacific),及「跨大西洋」(Transatlantic)的經濟脅迫威脅。
本文認為,威權國家似乎正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中過程冗長、程序僵化、積案甚多,與大國政治競爭複雜的弱點,擴展其經濟脅迫範圍。研究顯示,當前「爭端解決機制」中第一輪的專家「小組」(Panel)判定,需約15個月的時間完成調查報告,無法針對突發的經濟脅迫事件立即反應。[7]「爭端解決機制」中的「上訴機構」(Appellate Body),目前更因被美國認為其逾越美國主權而遭受抵制,功能停擺。[8] 即便案件通過爭端解決「小組」之判定,與「上訴機構」審核,案件最後的報告書尚需通過,由全體WTO會員組成的「爭端解決機構」(Dispute Settlement Body)決議採認,方可產生法律拘束力。整體來說,WTO的「爭端解決機制」並無法有效遏止威權國家的經濟脅迫行為。國際間需要新的組織,解決「經濟安全」的問題。
三、「經濟版北約」可強化供應鏈韌性與提升經濟發展能量
「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學者格雷(C. Boyden Gray)表示,「經濟版北約」的設立不應侷限於「經濟安全」的危機處理,該聯盟可強化盟友之間的供應鏈韌性與提升經濟發展能量。 「經濟版北約」的設立,對外可產生「拒止性嚇阻」(Deterrence by Denial)的效力(被嚇阻方可能因為經濟脅迫難以成功而放棄行動),對內可利用聯盟作為平台,調和盟國的經貿利益與法規,促進產業合作。[10]
前「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持相同觀點。[11] 「經濟版北約」聯盟的建立將為民主陣營夥伴帶來重建產業供應鏈,不過度依賴中國,與強化經濟韌性的戰略機會。太西洋與印太區域的經濟動能也將獲得新的合作發展機會。經濟的利多也可吸引更多理念相同的夥伴加入,壯大聯盟的經濟版圖,傳達經濟脅迫不易成功的訊號,遏止威權國家操作惡意制裁的意圖。
參、趨勢研判
建立「經濟版北約」之前景充滿挑戰與變數
現階段各界對於建立「經濟版北約」的集體「經濟安全」制度仍處評估與討論階段,距離實際落實與成立該機制尚有很長的路程。本文提出三點觀察,概要為何「經濟版北約」的推動將遭受挑戰。
首先,歐洲國家高升的「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意識,將阻礙推動橫跨大西洋與印太區域「經濟安全」聯盟的建立。歐洲國家在國際事務上的觀點與價值並不完全與美國同調。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與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近期表示,歐洲不應成為美國的追隨者。[12] 事實上,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2021年12月時,已率先提出反制外國經濟脅迫的「反脅迫工具」(Anti-Coercion Instrument)法案。[13] 歷經一年以上的討論,該法案於2023年3月28日獲得階段性的共識,賦予「歐盟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判定其組織或會員是否成為經濟脅迫對象之權利,與面臨經濟脅迫時可採取的集體反制措施。[14] 下一階段將進入法規調和與制定的技術層面。換言之,在歐盟「反脅迫工具」已取得階段性進程的條件下,歐美在短期內聯合成立「經濟版北約」的機會渺茫。
其次,若「經濟版北約」的成員數量真如倡議者建言,廣納橫跨大西洋與印太區域的民主夥伴,則會產生聯盟是否可履行承諾的「信用」(Credibility)疑慮。集體「經濟安全」保護的範圍越大,受到挑戰與「信用」測試的機會就越多。各種跨區域與產業鏈的經貿脅迫之判定、調查,與集體反制決策,將形成巨大成本,造成內部對立,影響聯盟的永續性。若「經濟版北約」因各會員國在經濟上的高度競爭,與對可負擔成本的不同意見,無法顧全廣大會員國的各別案件,落實「經濟安全」承諾,聯盟終將失去信用。
最後,經濟脅迫手段及形成與軍事侵略相比較不易界定。威權國家的經濟脅迫充滿灰色地帶操作,遊走法律邊緣。許多時候更透過假訊息、不固定的邊境檢驗、貿易阻礙等手段,試圖影響經貿氣氛,形塑有利脅迫方的認知環境。如何界定經濟脅迫案件的成立、程度與不同的反制方式將係難題。若採取嚴苛的定義標準,預計反制效用不大。然寬鬆的界定可能在聯盟機制上造成龐大負擔,易產生疲乏,影響履行集體承諾的信用。整體來說,「經濟版北約」建立之前景依舊充滿不確定性,需要持續的追蹤與觀察。
[1]Matthew Reynolds and Matthew P. Goodman, “Deny, Deflect, Deter: Countering China’s Economic Coercion,” CSIS, March 21, 2023, https://shorturl.at/hnPS1.
[2]“Liz Truss Urges Economic Nato’ to Stand Up to China,” Guardian News, February 17, 2023, https://shorturl.at/hjtyQ.
[3]Anders Fogh Rasmussen and Ivo Daalder, “Memo on an Economic Article 5,”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June 2022, https://shorturl.at/bhX57.
[4]Bernd Lange, “Instrument to Deter and Counteract Coercive Actions by Third Countries,” European Parliament, 2021, https://shorturl.at/fjotP.
[5]“Declaration on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cerning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 General Assembly, 1970, https://shorturl.at/oLSY6.
[6]“Charter of Economic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3281 (XXIX),” UN, December 12, 1974, https://shorturl.at/hqvBD.
[7]“The Dispute Settlement Crisi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ssues, Challenges and Directions,” Research Outreach, March 27, 2020, https://shorturl.at/tvP27.
[8]Simon Lester, “Ending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Crisis: Where to from Here?” IISD, March 2, 2022, https://shorturl.at/boHK9.
[9]C. Boyden Gray, “An Economic NATO: A New Alliance for a New Global Order,” Atlantic Council, February 21, 2013, https://shorturl.at/cADRX.
[10]同註9。
[11]Anders Fogh Rasmussen and Ivo Daalder, “Memo on an Economic Article 5,”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June 2022, https://shorturl.at/ovxQ8.
[12]Sagar Kar, “Macron’s Call For Strategic Autonomy Finds Resonance Among Many, Says Charles Michel,” Republic World, April 12, 2023, https://shorturl.at/rFGNS.
[13] “Commission Welcomes Key Progress in Trialogue on Anti-Coercion Instrument,” Directorate-General for Trade, March 28, 2023, https://shorturl.at/dmIQZ.
[14]同註13。